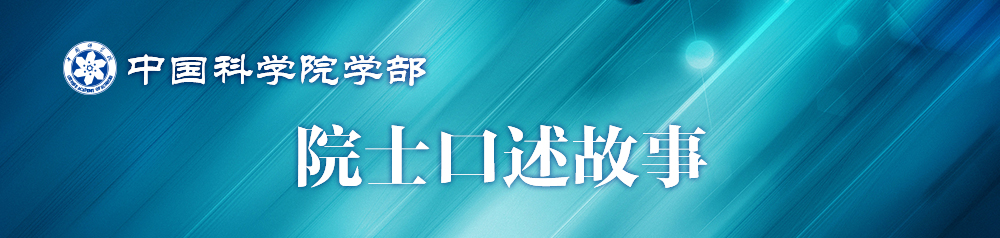戴汝为:高山仰止永为我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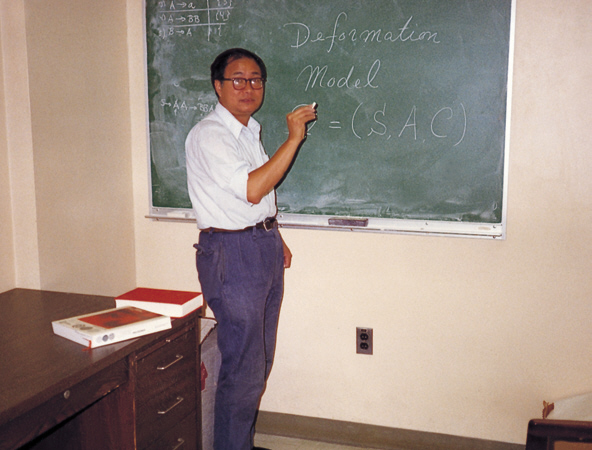
1980年,戴汝为作为国家首批访美学者在美国普渡大学作学术报告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我幼年正值抗日烽火,随母亲住在昆明西南联大校舍,母亲讲到某些知名教授放弃了国外安定的优越生活,携带家眷回到战乱中的昆明,来到由北大、清华、南开从北平迁到昆明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享受”这微薄的米贴(无工资,只发给购米补助),向我灌输了要敬重教授们的爱国精神和高深的学问,这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就读于西南联大附小、西南联大附中,受到西南联大特有的校风和那种睿智的感染,自己认定了要爱国、要走科学的路,向往得到像联大的大师们的教导。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迁回北平。我17岁高中毕业,从昆明北上,跨入了多年向往的清华大学,我国高等院校调整,又转到了北京大学。
1955年,钱学森在周总理直接关怀下,冲破重重阻碍返回祖国,任力学所所长。我刚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工作,记得共有4名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力学所。而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批国外高级知识分子回到祖国。力学所的高级研究人员多于大学毕业生,所以每个毕业生全能得到一位高研作为导师。我幸运地被分配到钱学森门下,在大师教导下从事科研工作的愿望实现了。钱学森回国在力学所的第一项学术活动,就是在中关村,对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及北大、清华等校的青年教师讲授他于1954年在美国出版的专著《Engineering Cybernetics》。钱学森让我学习工程控制论,听讲课并且与何善堉两人,整理笔记。钱学森刚回国时,虽然公事繁忙,但对讲课十分重视,我们两人把整理好的笔记,送交他过目,经他修改,再用油印机印刷成讲义后,发给大家。对于没听懂的内容,仍不清楚的地方,只好硬着头皮,向他请教,而且还大胆地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当时,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向科学大师学习可以说十分幸运,而且与他有较多的接触并有机会请教。我与何善堉又遵照他的指导,参照原文,整理讲义,并吸取苏联科学家对工程控制论的俄文译本中引用的俄文文献。1958年钱学森举世闻名的《工程控制论》中文译本,在德文译本和俄文译本之后终于在国内问世。
由于学习了工程控制论,对自动控制有一些了解,在钱学森的安排下,何善堉与我两人从力学所转到自动化所,成为1956年新建的自动化所的成员。1962年,中国科技大学的高年级学生从玉泉路到中关村。在著名科学家云集的中关村,有机会听科学家们讲课。由于我在钱学森的指导下掌握了工程控制论方面的知识,又对当时自动控制的一些新理论做了一些工作,因此被安排到科大自动化系给理论专业的学生讲授《最优控制课程》,成为科大最年轻的兼职教师之一。这阶段我在自动控制理论与应用领域,进行了十余年的研究工作。1980年,我赴美国Purdue大学作访问学者,进行了关于模式识别的研究,两年后返回北京。在关肇直的追悼会上,遇到了钱学森。这次见到钱学森时,他已经离开了中国科学院,我把在美国完成的五篇关于模式识别方面的论文,寄给了他,请他指教。由于钱学森十分关注思维科学的研究,尤其是形象思维的工作,所以对与形象思维密切联系的模式识别很感兴趣,通过回信,得知对我在国外完成的工作给予了好的评价与鼓励,从此开始了多年与他在学术问题方面的通信。这种直率、平等的通信交流,使我沿着钱学森所倡导的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和构建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的研究道路不断前进。在这个过程中,钱学森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对科技前沿问题的敏锐把握为我树立了一个向科学进军的学习榜样。
1986年,国内开始实行“863”计划,其中重要的领域之一是信息领域中的863-306主题,即智能计算机主题。当时的国际背景是,我们的邻国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实施了一个模式信息处理计划,即PIPS(Patter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计划,并于1978年在京都举行的第四届国际模式识别大会上,展示了PIPS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又提出第五代计算机计划,即KIPS(Knowled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计划,扬言以知识信息处理系统向世界挑战,从而把人工智能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正因如此,国内对研制智能机抱以很大的期望。这时我正在遵照钱学森的安排,为开展思维科学研究组织讨论班,同时被选为智能计算机主题专家组的负责人之一。钱学森给予建议:“暂时停止思维科学讨论班的组织等工作,作战略转移,全心投入智能机专家组的工作”,于是我在智能接口方面潜心研究了五年。在智能机的研究过程中,最重要且具有长远影响的,是钱学森于1991年4月18日与我及汪成为、于景元、王寿云的谈话:“今天我想说的中心意思是:智能计算机是非常重要的事,是国家大事,关系到下一个世纪我们国家的地位,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将有深远的影响。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不是智能机,而是人机结合的智能系统。不能把人排除在外,是一个人-机结合的智能系统”。这次谈话使我把后来的科研重点放在了人-机结合的智能系统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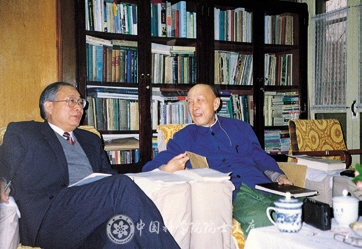
1995年,戴汝为(左)与钱学森(右)探讨思维科学的发展问题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1990年,钱学森等在《自然杂志》第13卷第1期发表了“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一文。之后认为在处理开放复杂巨系统的综合集成法方面,有不够完善之处。钱学森在学术上是十分严谨的,1990年10月16日,在北京国防科工委系统所举行了系统学讨论班,钱学森作了《再谈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报告,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改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我也作了题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技术》的报告。会后,他向我提出把上面两份报告整理成文,送交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杂志。该杂志于1991年第1卷第4期正式发表,对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作了准确的阐述。
1992年,钱学森进一步把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加以推广,3月13日给我的信中写到:我们的目标是建成一个“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这是把专家们和知识库信息系统、各种AI系统、几十亿次/秒的巨型计算机,像作战指挥演示厅那样组织起来,成为巨型人机结合的智能系统。组织二字代表了逻辑、理性,而专家们和各种AI系统代表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非逻辑、非理性智能,所以这个厅是21世纪的民主集中制工作厅,是辩证思维的体现!他提出我们现在要开拓的第三个时代——人机结合的大成智慧工程与大成智慧学。
我仔细考虑了钱学森提出的宝贵意见,1995年,我把综合集成的构思推广到智能系统的综合集成,并且作为“智能自动化丛书”的第一册,由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书呈送给钱学森,他收到书后给他领导的学术集体的王寿云等6人写了一封信谈到:信息革命实是产业革命,即我们所说的第五次产业革命,所以这部《智能自动化丛书》,也可以说是一部第五次产业革命的丛书。在丛书第一册就把一切智能系统放在我们说的“大成智慧”和“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来思考。从而把我们的理论同第五次产业革命联在一起了,这封信是钱学森对我们的学术团队所完成的工作给予的评价,使大家深受鼓舞,紧接着这个学术团队把人机结合,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应用于汉字识别的研究,着眼于尽量利用人的聪明才智,形成了集成型汉字识别系统,这种系统较之其他方法具有更高的识别率。由于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在信中就得到钱学森关于人机关系的看法,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不断请教并琢磨有关以人为主,人机结合,从而开展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的工作。我先后承担了“863”项目、“攀登计划”项目,从1999年起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重大项目“支持宏观经济决策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充分利用专家群体的智慧,并以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为基础,把研讨厅从“大厅”扩展到信息空间,钱学森称之为“智界”,从而构成基于信息空间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Cyberspace for Workshop of Metasynthetic Engineering),实现了大成智慧的涌现。
回顾50年前钱学森排除艰危毅然回国,在国防战线和科学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通过聆听他的教诲,使我在开展人-机结合智能科学研究和实践大成智慧工程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道路上不断前进。钱学森学术思想的前瞻性和为国家科技发展呕心沥血的赤子之心是我们终生的榜样。高山仰止,永为我师。
(节选自《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2006,(02):9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