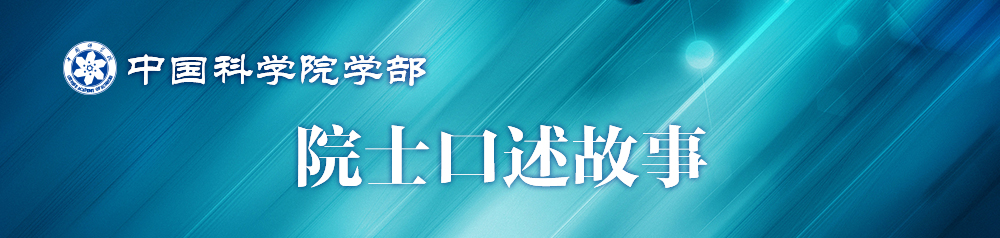王承书:一生回顾 几点希望

回国不久的王承书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1912年6月26日,我出生于上海一个封建家庭。父亲早年考中进士,后被清政府选派赴日留学,民国初年曾任内务部警政司司长兼警官高等学校教授。
我从四岁半入学直至大学毕业,一直在教会学校就读。我的童年家庭看似简单,实则关系复杂,这使我从小对封建礼教产生反感。学生时代,正值国家外受列强欺凌,内遭军阀与反动政府统治,目睹时艰,内心充满忧愤,逐渐形成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正义感。
1941年至1956年,我在美国求学和工作。我学习刻苦,律己甚严。想到祖国同胞身处水深火热,我在海外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内心无时无刻不盼望着早日回国效力。
新中国成立后,因美国政府实施禁令,我被迫滞留异国。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我内心经历长期挣扎,最终下定决心:宁可被关进集中营,也绝不做任何损害祖国利益的事。此后五年间,我对祖国的关注与日俱增,归心似箭。
1956年10月6日,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在阔别十五载的国土上,我第一次望见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内心激动难言——这才是我人生真正意义的开端。
从1958年底起,我决心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主人翁意识开始萌发。
1958年至1961年春,我投身受控聚变反应及等离子体物理研究,参与填补国内该领域空白的开拓工作。我与青年科研人员共同调研学习,带领团队完成了原子能研究所两项受控聚变装置的物理设计与参数选定。
1961年3月,我因国家需要转向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在自学钻研的同时,培养理论队伍,在多个关键领域播下种子,为后续工作奠定基础。1962至1964年间,为我国首座铀分离工厂启动开展系列理论研究,参与级联定态与动态计算分析。1964年担任4号机总设计师,主持参数选定等关键工作。1969年后参与指导扩散机改进及新厂级联设计。

王承书(右三)与科技人员研讨工作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1972年后我逐步减少具体科研,主要指导理论研究工作。担任国家“七五”攻关项目“离心法”与“激光法”分离铀同位素专家组组长,在原子能研究院推动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学科领域,着力培养科研方法与作风。
虚度八十寒暑,归来已三十六载。虽略尽绵薄,然因主客观所限,未竟当年报国之志,深愧于党与人民。自知余日无多,生命本就是一场消耗。我这一生,事业占据生命三分之二,为此舍弃了女性理应对家庭的付出。但我从不后悔——须知事业与家庭,于女子终难两全。
死生有命,期不可知。谨以“笨鸟先飞”之诚,预陈数愿:
1.不要任何形式的丧事;
2.遗体不必火化,捐赠给医学研究或教学单位,希望能充分利用可用的部分;
3.个人科技书籍及资料全部送给三院;
4.存款、国库券及现金等,除留8000元给未婚的大姐王承诗补贴生活费用外,零存整取存款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其余全部捐给“希望工程”;
5.家中一切的物件,包括我的衣物,全由郭旗处理(注:郭旗系王承书院士的儿媳)。
(根据《物理教学》2008年第2期文稿整理)